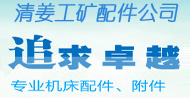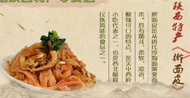宝鸡,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中华文化的兆始地之一。两千年来周秦时代的文言遗风仍然保存在宝鸡的方言中,这里就平时从宝鸡方言中领悟到的周秦文言雅韵与大家共享。 -----王明生
吾 吾,现一般读wú。对吾的解释,《新华字典》:“我,我的。”《说文解字》:“我,自称也。从口五声。” 吾,宝鸡方言读做yá,不但有我、我的意思,还有咱、咱的意思。这充分反映了宝鸡人自古就具有的“我即咱,我的即咱的”的博大胸怀,唐人柳宗元誉始皇帝之“公天下”是也。 吾yá,《康熙字典》:“《集韵》牛加切,音牙。允吾,县名。《前汉•地理志》金城郡允吾县。《注》应劭曰:允吾,音鈆牙。”《后汉书》颜师古注:“允吾,县名,属金城郡,故城在今兰州广武县西南。允音沿。吾音牙”。《水经注》:“允吾县在大河之北,湼水之南。”允吾县,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置,为金城郡治。治所即今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马场垣乡下川口村。一说在今甘肃永靖县西北。三国魏废。前凉复置,仍隶属金城郡。前秦、后凉、南凉、西秦、北凉沿置。北魏时废。 又,衙yá,形声字,用吾yá声。《说文解字》:“衙,行貌。从行吾声。音牙。”《康熙字典》:“《集韵》、《韵会》牛加切,音牙。《广韵》衙府。《类篇》古者军行有衙,尊者所在,后人因以所治为衙。”知衙做为衙门、官衙之称为借用。 以上,吾读做yá已有确切出处。 再说中华第一古物――石鼓及其文字中《吾车》、《吾水》篇中吾的读法。石鼓,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关于石鼓产生的确切年代,几千年来学者讨论不断,提出各种看法,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被大家都赞同的确定的结论。现有多位学者认为它是秦景公时的作品,也有论点认为是秦襄公、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秦献公、秦惠文王、始皇帝等说,莫衷一是。无论何时所刻,它的出土地在现宝鸡市区的石鼓山已经无疑。宝鸡,无论在秦的早期,还是在秦惠文王时期,都是秦国的腹地,若是始皇帝时更不用说。石鼓诗歌通过从秦之建立、立国、发展、创立伟业这一发展顺序,歌颂了对秦人的历史发展进程有重大贡献的先相烈公的重大历史事迹。十篇“石鼓文”,既歌古也颂今,用诗歌描绘出一幅幅形象生动的秦人创业发展的历史画卷。既是在秦国的腹地而不是在国境以外,歌颂自己的先祖,就没必要称吾wú(我,我的),而应更确切地称吾yá(咱,咱的)。所以,《吾yá车》篇应读作“吾yá车既工,吾yá马既同,吾yá车既好,吾yá马既辅”。这样的读法,只有在石鼓的产生地才能感受到当时秦公一行及其作者的心情。
大、娘 宝鸡方言称父亲为大dá、称母亲为娘niá。 大,《说文解字》: “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古文亣(他达切)也。”宝鸡方言称父亲为大,可能因为宝鸡的先人们认为“天大,地大,人亦大”,称自己的父亲为大,充分体现了宝鸡人的早期文明。那么称自己的父亲为大,天大、地大又怎么处理呢?宝鸡人有办法:给天、地升格,称天为“天爷”或“老天爷”。如宝鸡人把天下雨叫“天爷下雨了”,天晴叫“天爷晴了”,天阴叫“天爷阴着哩”,把太阳叫“爷头”(即太阳为天的头)等。地,脚下无处不“地”,怎么办?把“土地爷”供起来,至今,宝鸡的广大农村家家户户在门里的照壁上都设有土地堂供奉着“土地爷”。这样,说就置天、地于父亲之上。 称娘niáng为niá,是因为人、神有别。中国自古是多神崇拜、泛神崇拜。宝鸡作为华夏文明的兆始地,更不可能例外。现境内还有非常多的敬奉众多女神的庙宇或遗存,除过供奉观世音菩萨的寺庙外(可能与观世音菩萨是秦以后由外传入的神祇有关,且传入之初观世音菩萨并非女性),宝鸡人统称为娘娘(niáng niáng)庙。最古老的当属凤翔县槐原的女登祠。女登传为华夏始祖炎帝之母,宝鸡是炎帝故里。宝鸡人不但祠炎帝,更祠其母。椐凤翔女登研究会考证,槐原女登祠始建于周,兴盛于唐,清嘉庆二十一年再次扩建(有嘉庆二十一年碑文证)。可惜在“文革”中祠损像毁。女登祠当地人就称为娘娘(niáng niáng)庙。另外,宝鸡还有叫做娘娘(niáng niáng)庙的地名。在这里,同一个娘字,称神为niáng,称母为niá。 由此可知,宝鸡人称女神为niáng,称自己的母亲为niá,充分体现了人、神有别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也可能开了避帝王名讳之先河。宝鸡深厚的文化底蕴由此可见。 另外,宝鸡人称父亲的兄长们为大伯、二伯、三伯等依次类推。伯bǎi,《汉典》:“今北方方言称‘大伯子’”。《说文解字》: “长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凡为长者皆曰伯。”《释名》: “父之兄曰伯父。”伯的本意为“兄弟排行次序,”即兄弟们按伯、仲、叔、季排行。宝鸡人不管父亲有几位兄长,统称为伯,以示“长者皆曰伯”的尊敬。 称大伯、二伯、三伯的配偶为大大、二大大、三大大等,依次类推。大大读dāda,后读轻声。大大,在方言中,有的地方称父亲为大大,有的地方称祖父为大大,而唯独在宝鸡称伯父的配偶为大大,其中之意,耐人寻味。是否与“长兄比父”相关?抑或与称呼的性别、奇偶数相关?已无可考,细究起来,只觉其文化含义极深。 宝鸡方言称父亲的弟弟辈们为爸或爸爸,若父亲的弟弟辈人数多,则前加排行依次称呼。爸bà,《新华字典》:“称呼父亲。”《玉篇》:“父也。”《正字通》:“夷语称老者为八八,或巴巴。后人因加父作爸字。”《广雅疏证》:“爸,父声之转。爹,北人呼父也,(上父下者,古字,实在打不出此字)吴人呼父也”。《集韵》:“吴人呼父曰爸。”《广韵》:“爹,北方人呼父,与南史不合。”可知在古时,爸的称呼乃东夷和南方吴楚之音,并非中原华夏之称。因古时华夏族有卑视“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习惯,故而称呼小于父亲的父辈们用“四夷”之称曰“爸”或“爸爸”,以示与伯、大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名称上,而且还体现在等级上。 宝鸡方言把“爸”或“爸爸”的配偶叫做“娘娘”,读做niá niá。最早为什么如此称呼,也无从考证,现在只觉得将“爸爸”的配偶叫做niá niá,既可使人、神有别,又可做到长、幼有序。宝鸡的文化积淀由此可见一斑。有趣的是,今年春节期间陕西演员苗阜、王声的相声演出,使niá niá一词风糜全国,炎帝的女儿说“niá niá,风浪太大了。”周朝时皇帝登基坐殿,一张口“niá niá,有事早奏,无事退朝。”虽为调侃,但当是有其历史渊源的。由此可知,不懂宝鸡方言的人把niá niá一词等同于现代口语中的“我的妈呀”,是值得商榷的。
婕婕 宝鸡人把未出嫁的女孩子统称为婕婕jièjie(后读轻声)或婕婕娃,出嫁后,统称为媳妇。如:“你媳妇生了个儿子还是婕婕?”现在多讹写为“姐姐”。 婕jié,《说文解字》: “女字也。”《集韵》:“美貌。”《正韵》:“婕妤,妇官。”婕妤,《汉书》也作倢伃。《新华字典》:“婕妤,古代女官名。”宝鸡方言将小女孩称为婕婕,除与其形容美貌有关外,还可能与中国自古就有的官本位、崇官思想有关系,因为这样称呼,饱含着长辈对孩子们未来的美好希冀。
咥 咥dié,《新华字典》解释:“【动】 咬;啮。”《易•履》“不咥人亨。郑注:‘咥,啮也’”。宝鸡人所说的“咥”,不但有咬、啮的意思,更多的是吃、食的意思。如明人马中锡《东田集•中山狼传》:“狼曰:‘第问之,不问将咥汝’。”咥,流行于男人者多,有点现在所说“大吃大喝”、“海吃海喝”的意思,一个咥字,充分体现了古秦人的豪爽与激情。
挕 挕dié ,宝鸡方言称打为挕。如我把他挕了一顿。 挕,《新华字典》:“打”。《康熙字典》:“《篇海》丁叶切,音喋。打也。”
彘 宝鸡方言称猪为彘。彘zhì,《汉典》:“象形。小篆字形。矢声,其余象猪头、脚。本义:彘本指大猪,后泛指一般的猪”。《新华字典》:“彘,猪:狗彘不如。狗彘不食。”《说文解字》:“彘,豕也。后蹏废谓之彘。从彑矢声;从二匕,彘足与鹿足同。直例切。”豕亦猪,蹏同蹄,彘足与鹿足同,即同为偶蹄动物。《小尔雅》:“彘,猪也。”。《贾子胎教》“彘者,北方之牲也。”《山海经•西山经》:“竹山有兽焉,名曰毫彘。注:‘毫彘,吴楚呼鸾猪。’”可知宝鸡人把猪读做zhì,并不是字音读错了,而本来就不是同一个字。彘,是一种很古老、很文雅的称呼。 彘当为北方的称呼,周、秦时雅言、国语。称彘为猪,应是南方吴楚之音。
霈雨、霖雨 霈雨,是宝鸡人对暴雨、雷阵雨的叫法。现多讹写为“白雨”。因为宝鸡方言将白读做péi。 霈pèi,《汉典》:“【形】。形声。从雨,沛声。本义:大雨。雨、雪等盛大的样子。也作‘沛’”。《玉篇》:“霈,大雨。”《孟子•梁惠王上》:“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 霖雨,宝鸡人对久下不停的雨、连阴雨的称呼。 霖lín,《新华字典》:“久下不停的雨:霖雨。霖沥。霖霖。”《说文解字》:“雨三日已往。从雨林声。”。《尔雅•释天》:“久雨谓之淫,淫谓之霖。”《左传•隐公九年》:“凡雨三日以往为霖。” 宝鸡人将暴雨、雷雨称做“霈雨”, 将久下不停的雨、连阴雨称“霖雨”,也是一种很古老、很文雅的称呼。
一庹、一帀 宝鸡人对长度单位的一种约略称谓。如,这个桌子有一庹长;这套书有一帀厚。 庹tuǒ,《汉典》:“【量】。中国一种约略计算长度的单位,以成人两臂左右伸直的长度为标准,约合五市尺。”《字汇补》“音托。两腕引长谓之庹。” 帀zā,《说文解字》: “周也。”《汉典》:“【量】同‘匝’, 环绕一周叫一匝”。宝鸡人所称一帀,是其引伸义,即以拇指和食指环绕一周的周长作为概略计算长度的单位。 用一庹、一帀作为一种约略计算长度的单位,不借助任何工具即可计算物体的长度,而且人人基本通用,既方便,又实用,是古时宝鸡先人们的智慧结晶。
枵薄 宝鸡方言对衣物等透薄的称谓,后又衍变为某种对象不耐用或某人身体瘦小、单薄、不健康的叫法。如,这人身体枵薄得很。 枵xiāo,《新华字典》:“⑴空虚:枵腹。外肥中枵。⑵布的丝缕稀而薄:枵薄。”《说文解字》: “虚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枵,木大貌。庄子所云呺然大也。木大则多空穴。” 薄báo,《新华字典》:“厚度小的。” 既空虚而且厚度很小,宝鸡方言叫做枵薄,很古很雅。
奅 奅pào,宝鸡方言称虚而大为奅,如,这新掐的苜蓿菜虚奅奅的,其实没重量。引申之也称虚胖的人,如,这人身体奅着哩。 奅,《新华字典》:“虚大。”《说文解字》:“大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此谓虚张之大。”《史记•建元以来侯者表》:“南奅侯公孙贺。” “虚张之大”为奅,很古的用字。西汉去秦不远,尚有用者,现在书面多已不用,仅存于宝鸡的方言之中。
覛 覛mì,宝鸡方言把不正眼看人叫覛,如,我覛了他一眼;把小眼睛叫覛覛眼。也当眼字用,如宝鸡方言把没眼色叫没覛眼。 覛,《新华字典》:“⑴看,察看;⑵古同“觅”,寻找。” 《说文解字》:“衺(邪)视也。”《国语•周语》:“古者太史顺时覛土。”
捯饬 捯饬dáochì,宝鸡方言把不停地、反复地摆弄某一物件叫捯饬。 捯,《新华字典》:“两手不住倒换着拉回线、绳等。” 饬,《新华字典》:“整顿,使整齐。”《说文解字》:“致坚也”。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致之于坚。是之谓饬。考工记曰,审曲面势以饬五材。谓五材皆必坚致也。又曰,饬力以长地材。谓整顿其人力也。凡人物皆得云饬。饬人而筋骸束矣,饬物而器用精良矣。其字形与饰相似。故古书多有互讹者。饰在外,饬在内,其义不同。”
颇烦 颇烦,是宝鸡人对不耐烦、心烦的称谓。颇字的用法同于颇为出色、颇多、颇少、颇佳、颇甚、颇为得体等的用法,是一种很文雅的修辞法。 颇pō,作为形容词,本义如《说文解字》: “颇,头偏也。”如《史记•匈奴列传》:“天不颇覆,地不偏载。”即俗说之不偏不颇。作为副词,《新华字典》的解释是:“(1)略微、稍;(2)很、甚。” 以上可知,宝鸡方言所说的颇烦,极富修辞的美感。从颇的本义上讲,可以理解为偏烦。颇若作为副词理解,则可以囊括烦躁的不同程度,如略微有点烦、稍稍有点烦、很烦、特别烦等。
麻乱、麻怛ma da。 宝鸡方言称心情不好、心烦、烦躁不安为麻乱。如,今天心里麻乱的很。称事情难办、事情复杂、头序纷乱、事情发展的后果很严重或某人难打交道为麻怛。如这事麻怛大了;这人麻怛得很。 麻乱,《新华词典》:“烦乱;纷乱。”《汉典》:“纷繁杂乱;混乱。”如陕西作家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题叙:“ 生宝他妈,我心里麻乱得慌。” 麻, 《新华字典》:“【形】⑴形容众多,混乱;⑵表面粗糙的、凹凸不平的;⑶带细碎斑点的。【动】⑴穿丧服。《礼记•杂记》:‘麻者不绅。’⑵麻木。⑶感觉神经受压迫,暂失知觉。” 怛,《新华字典》:“⑴忧伤,悲苦。⑵惊惧。”《说文解字》: “怛,惨也。”《增韵》“惊也,惧也。”《释文》:“怛,惊怛也。”《广雅》:“怛,忧也。”《诗•齐风•甫田》:“劳心怛怛。” 麻怛一词,作为形容词,也是一种很古老、很文雅的用法。
憥忉 宝鸡方言称某人难打交道为憥忉láo dāo。如,这人憥忉的很。某些方面可与上文“麻怛”互通。现多讹写为“唠叨”。 憥láo,《新华字典》:“心力疲乏。”。《玉篇》: “心力乏也,疾也。” 忉dāo, 《新华字典》:“形容忧愁,焦虑的样子,如‘无思远人,劳心忉忉。’”《广韵》、《集韵》:“忧心貌。”。《诗•陈风》:“心焉忉忉。” 憥忉一词,形容与这个很难打交道、但又不得不与之继续打交道的一种忧心、忧愁、心力憔悴的无可奈何的状态。憥、忉及上文提到的怛,都是古语用词,现已不用,或极少用到,但在宝鸡方言中,仍然时时在用。
鬌脑duǒnao 鬌脑,宝鸡方言对头的称谓。 鬌,《新华字典》:“头发美好的样子”。《汉典》:“鬌,小儿留而不剪的一部分头发”。《说文解字》: “发隋也”。《康熙字典》:“鬌,音朵。《玉篇》:小儿剪发为鬌。《类篇》:剃余发。一曰发美。《礼•内则》剪发为鬌。《注》鬌,所遗发也。《疏》三月剪发,所留不剪者为鬌。” 脑,《新华字典》:“⑴高等动物神经系统的主要部分,在颅腔里,主管感觉和运动。⑵头:脑袋。脑壳。《说文解字》:“本作匘。头髓也。” 宝鸡方言鬌脑,当为对小儿的头的爱称衍变而来,用鬌――小儿所留下不剪的、美丽的、头上最醒目的“髻鬌”与头的主要功能“脑”组合为头的代称,要比现在所称“脑袋”文雅得多。
补白 宝鸡方言把道歉叫做补白。宝鸡方言白读做péi。 补bǔ,《新华字典》:“⑴把残破的东西加上材料修理完整。⑵把缺少的东西充实起来或添上。”《说文解字》:“完衣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既袒则宜补之。故次之以补。引伸为凡相益之称。”《急就篇注》:“修破谓之补。” 白,《新华字典》中有“陈述”的意思。《玉篇》:“告语也。”《正字通》:“下告上曰禀白。同辈述事陈义亦曰白。”《汉书•高帝纪》:“上令周昌选赵壮士可令将者,白见四人。” 补白也罢,道歉也罢,都是在说了对不起别人的话或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之后的“次之以补”的行为,即“修破谓之补。”显然,补白的遣辞造句,不但要表示歉意,而且还说明这是一种“次之”、“修破”的行为,比道歉的遣辞更为切贴。
嫪连或嫪恋 宝鸡方言对牵挂、依恋不舍的称谓。如,这娃走了几个月了,也没个信,把人嫪连得。 嫪lào,《新华字典》:“惜恋。”《说文解字》:“婟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声类云:婟嫪,恋惜也。
瞅视、盯视 宝鸡方言把东张西望叫瞅视,把目不转晴叫盯视。多么简洁明了。
颡眼 宝鸡方言对馋眼、喜欢什么东西时的目不转晴、特别是小孩对好吃的东西踮足翘首地盯视行为的称谓。如,这娃颡眼sǎngyan得很。 颡,《新华字典》:“额,脑门儿。”《说文解字》:“额也”。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方言。中夏谓之额。东齐谓之颡”。知颡为对额的方言称谓。只不过段玉裁先生做为祖藉安徽的江苏人,在贵州、四川做过官,可能没有到过周秦的发祥地,不知源头上就有此方言。东齐的“颡”还可能是东齐之祖姜太公从宝鸡带过去的也未可知。或者,当周秦之时,颡本为正声,而额为方言也是可能的。 颡眼sǎngyan的遣词造句比之目不转晴等同意词更为切贴,更为形象。颡眼,不仅有眼晴的盯视,而且有全身的动作:踮足、翅首。即便是如此还嫌不够高,恨不得把眼晴长到“颡”上去。因为颡为头前部的最高位置,如果再往上长,意思又完全变了,宝鸡方言叫“眼晴长脑顶去了”。即眼晴只朝上看,而看不见前边。宝鸡方言如此生动。
爨 宝鸡方言对鼻子嗅到的气味、特别是香味的一种简洁的形容。如,你闻闻这韭菜爨cuàn得很。 寁劲 宝鸡方言对某人、特别是小伙子很迅捷、机灵、能干而且人又长得佼好的称谓,近几年比较流行的“给力”一词较接近。如,这小伙寁劲zǎnjìn得很。 寁zǎn,《新华字典》:“迅速;快捷。” 《说文解字》:“ 居之速也。” 《广韵》:“亟也。”《诗经•国风•郑风•遵大路》:“无我恶兮,不寁故也。” 谝 谝piǎn,《新华字典》:“(1)花言巧语。(2)显示,夸耀”。 《说文解字》: “便巧言也。”《类篇》:“辩佞之言也。”《书•泰誓》“惟截截善谝言。” 谝,在宝鸡方言中,更多地表现为显示、夸耀,即使有花言巧语的成分,也是善意地。若是有欺骗、诈骗成分的花言巧语,宝鸡方言则称之为“鬼话”,如“这人张口就鬼话连篇,肯定是个骗子”。是否有恶意这种尺度的掌握,宝鸡人是烂熟于心的。
嚚 宝鸡方言称人奸诈、狡猾为嚚。如,这人嚚得很。现在多讹写为阴。 嚚yín,《新华字典》:“⑴愚蠢而顽固。⑵奸诈。⑶有声而不能成语。”《说文解字》: “语声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左传曰,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引伸之义也。”
喝汤 宝鸡方言把吃晚饭叫喝汤。如,宝鸡人晚上见面的问候语是,“你喝汤了么?” 这可能因为是中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产生于岐地。《黄帝内经》以托名黄帝、岐伯、雷公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病机病理的同时,主张不治已病治未病,同时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年。因此,中医的养生、摄生观念早就深入秦地人心。喝汤,亦即现在人们所熟知的饮食养生中“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的良好饮食习惯,在秦之故地早已有之,因而将吃晚饭直接叫做喝汤。
毕了 宝鸡方言对完了、结束了的称呼。 毕bì,古作毕。《汉典》:“会意。甲骨文字形,上端象网形,下端是柄,古时用以捕捉鸟兽、老鼠之类的器具。金文又在上面加个‘田’,意思是田猎所用的网。本义:打猎用的有长柄的网。”《诗•小雅•鸳鸯》:“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宝鸡方言把完了、结束了叫做毕了,属名词动用。《新华字典》:“毕。【动】完毕,结束;全部使出。” 宝鸡方言说毕,而不说完,是因为“完” 还是古代一种较轻的刑罚之一。“完”作为一种刑罚,在汉以前指剪去犯人的须发,汉以后改为罚作劳役,因其不伤肢体,故称“完”。 如《汉书•刑法志》:“刖者使守囿,完者使守积。”因此,宝鸡方言不称完而称毕,很有可能是为了避开“完”同时作为一种刑罚名称的秽气。 宝鸡方言也说“完了”,但少有结束的意思,而更多的是等同于“坏了”、“不好了”的意思,更靠近于人被“完” 刑,有点被刑罚的味道。
就宜了 宝鸡方言把事情办妥了、任务完成了叫就宜了。 就,《新华字典》将之作为动词有“完成、成功”的解释。《说文解字》:“就,高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广韵曰。就,成也” 宜,《新华字典》::“适合,适当;应该,应当。”《康熙字典》:“宜,《说文》所安也。《传》宜者,和顺之意。《玉篇》当也,合当然也。” 就宜了,不但说事情已经完成了,而且完成的很恰当,很和顺,并且完全按要求达到了应该达到的目的。
上一页《《《 宝鸡市舆情资料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