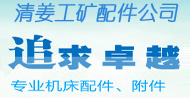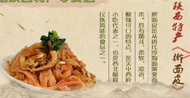文/樊志洲 在云南,因为民族众多,各种小吃多的尽乎无法记住,除非每次带着小本记录,才有可能数清楚云南的美食。但云南的吃,除汽锅鸡外,首先让人想到过桥米线。过桥米线现在已经通俗化了,国人皆知,最正宗的过桥米线来自于云南蒙自。一般满满的一大海碗,漂着厚厚一层黄澄澄的鸡油,看上去像冷的,舀一小勺递进嘴里,不小心会直烫舌头。下在碗里的配料除鸡丝及各种菌类之外,甚至还有海参、鱿鱼卷、鲜虾仁、蟹黄什么的,确实是地方名吃,真若天天吃这种过桥米线,油腻得一定让人想去洗胃。 最可口的米线,是在长江第一湾石鼓镇吃的。我去维西常路过那里,原本在剑川吃饭却错过时辰,刚好到了石鼓镇赶上饭点,在红军渡口的码头边,有一些卖米线的地摊。就要了一碗填肚子,摊贩把米线在汤锅里烫了一下,就端上来,浇上一勺辣椒油烧牛肉片,挟一撮不知名的烫莱,味道喷香。没想到最可口的米线,居然是最朴素简单的米线,5块钱一碗。可能因为我饿了,吃得很舒畅。饱暖之后不禁浮想联翩,长江第一湾周围的风景很好,这里纳西、白族美女众多,大概就是吃这种米线长大的吧?美食,必定产生在有美女的地方。即使没有美女,也要有美景。 在云南除米线、普洱茶、乳扇外,在云南西北部中甸的白马雪山上,还有用手想触摸的云彩,“山涧铃响”越来越少存在的古老马帮,雪线下森林中数不清的各种菌子,当然最特色的还是村寨里的火塘。在各民族的村寨里,家家都有离不开的火塘。靠火塘做饭,靠火塘取暖,夜间还靠火塘照明。 我去过一个朋友家中,坐在火塘边,还可以用夹棍烤鱼、烤肉。通常将鱼或肉剖开,抹上各色调料,夹在特制的棍子上,伸入火塘中慢慢烘烤。饮食因为带有游戏般的可操作性,而充满乐趣。经久不息的火塘,上面支有铁三角架,吊着铁锅、砂锅啊什么的。锅里煮的什么,要等盖子揭开了才能知道,可我已提前闻到了泄密的香气。我还看见火塘边被映红的一张张面庞。火光使他们的表情更为神秘,也更为丰富。可是这些不知能保留多久?当下高度发达和快速传播的今天,马帮渐行渐远会消失,火塘会废弃,只能剩下残留多年的灰烬。当地人,迟早要改用煤气灶做饭。方便倒是方便了,是否也会缺少一些古老的乐趣? 尽管在这里吃了很多小吃和名吃,但能铭刻在心中的还是“长筷饭庄”的特殊经历。由朋友引路,吉普车驮着一伙兴奋的吃货们沿金沙江北行,沿途能看见篱笆围绕的农舍、江面上横拉的滑索和吊桥,在奔子栏拐向一处上山的小路,行驶约三、四公里,最终抵达山凹里森林茂密处一座孤零零的小农庄。这是典型的普米族风格建筑,整个房屋院落未用一砖一瓦,柱子、大梁和椽子自不用说,连墙壁和隔档都是用整块的松木制成十公分厚的木板套卯装成的,抚摸时仍有锛子的痕迹,到处透着松香气味。房顶是用大片的千枚岩铺就而成,在水气中闪烁着金属般光泽,这些就地取材都能得到,真有点返朴归真的感觉。站在这里极目远眺,已看不见脚下的金沙江,仿佛置身于云端里,由于海拨高、湿气浓、寒气重,感觉很有些“隐士”的味道。 由于事先打电话预约好,当我们一走进院落时,主人便热情地迎接招呼我们。大家进到厅堂围着“火塘”席地坐了一圈,看着主人在“火塘”上架上柴薪,支起大釜,放入香气腾腾的底料,不一会就云霭缭绕,暧意融融。 这时候主人托来大盘,依次放入火腿、山鸡、松耸、牛肝菌等主料,再放入红见手。不管是红见手还是黄见手,都有微毒,然而又极其美味,所以云南做法一定是重油反复加工的切薄片干椒或者青椒炒,汤煮便能去毒,当属非常另类。然后每人跟前放一个盘子、两付筷子,一长一短,长的约1米,短的就是普通筷子。主人开始认真介绍说:这“火塘”的火燃烧起来,火大热壮,短筷无法靠近,而长筷又无法自食,故尔你加我食,我加你食。这就是长筷的妙用!你们看,每付筷子都有字。我们仔细一瞅,果然每付筷子都刻着:“人人喂我,我喂人人!”想来甚有意蕴,也很有意义! 一会儿釜中黄澄澄的肥鸡和火腿一起翻滚着,里面夹杂着大块的黄见手,要么是完整的小骨朵,稍微大些的,最多一分为二,决计不会比麻将小。釜中奇香四溢,大家抄起长筷不停地问询对方:是要菌子,还是要鸡肉?不一会由生蔬到熟炼,场面逐渐热闹起来。咬一口那大块的菌,爽脆又多汁,鸡油包裹着,又滑嫩,吃起来有层次又相当分明。其实让人最感叹的一件事情,就是终于可以大块大块大口大口地吃黄见手了,所谓大快朵颐,不过如此。 这一轮刚刚结束,釜中仅残留了半指厚的油汤,主人加入约半釜多白开水,从新将火烧旺才告诉我们,真正的野鲜大宴开始了;主人从操作间揣出一个不锈钢大盆,上覆着粉、蓝二色鲜艳欲滴的磨菇,由于盆底用大量冰块作衬,放在火塘边也是冷气丝丝的。主人介绍说:这是至毒之物,也是至鲜之品,方法得当就可品尝到人间仙品。这种毒菌叫粉头和蓝头,非常罕见,只有在我们这里才有,倍受野派吃客的推崇。毒菌相当于中国饮食文化里的“禁果”,一种致命的诱惑,它的鲜美因为神秘与危险而被夸大。美食家们不仅没有望而却步,反而趋之若鹜。这份勇气,恐怕连渎职的亚当、夏娃都会自叹弗如。我这会儿也不由的“肾缐素”上涌,颇有点“舍命吃河豚”的劲头。 这时,将粉头和蓝头倒入釜中,加入矿盐少许略为搅动,主人解释道:这种菌子采摘时要靠冰块收敛毒性,然后大火沸煮半小时才可尽除毒性。半小时后,原来的的粉蓝颜色尽退,变成了蛋黄色和浅综色,形状比下锅时大了许多,汤色也粘绸起来。主家捞出一块先尝了一口,以示无毒放心食用,然后给每人碗里捞了几决,奇异浓郁的香气和黄澄澄的鲜美相辅相成,菌子嫩中带韧的口感和胀发的滑嫩形成奇妙的对比,李渔李笠翁,他嗜吃如命他说过:“予于饮食之美,无一物不能言之,且无一物不穷其想象,竭其幽眇而言之。”确令人百吃不厌。至于浓郁的菌汤,最适合泡一碗饭吃,小碗还不理想,要换中碗甚至大碗,那样才有饕餮的快感。 直到这时,我才体会到野外吃野味的乐趣。每当空气中带着泥土潮湿的芬芳的时节,就想起那云雾笼罩的高山,那山林间一朵朵隐藏的菌子,想起采摘那一刻的惊喜和艰辛,任何滋味也比不上那如同阵阵松涛拂过舌面的菌子清香,带着风、雨、雷电和一年的期待,小小的菌子蕴含着大自然慷慨的馈赠。靠老天赐予鲜美和清甜的滋味,所谓山珍,也不过如此。我很尊敬并羡慕那些在火塘边长大的人们,他们体会过真正的人间烟火,这里的一切不仅仅是长筷子所带来的思考,还有老天造物的神奇与宽厚,真心要善待这山中的珍宝了。 美食是一种经历,更是一种记忆。能在记忆里留住的美食,才算永恒。让你到老到死都忘不掉那一口儿。想起来就馋。恨不得能故地重游,旧梦重温。仿佛美食依旧在原地等你。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重新改于花城地下室 |